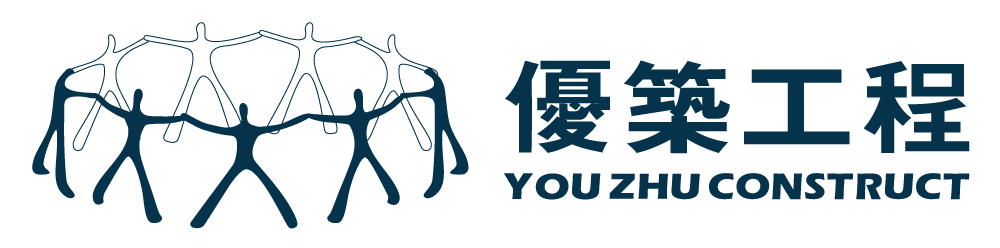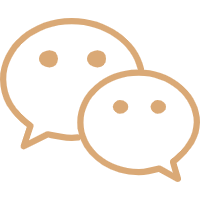严红波:
打造经得起推敲的装饰工程
木门柱,白墙不着一字,自己做的书柜,藤蔓爬在窗格上,泡茶的人抬起头,墙上的logo也是木的,一根一根,嵌在墙上。干了二十年装修,严红波新的装饰工程公司取名“优筑”,“我是个手艺人,在水泥钢筋中摸爬滚打二十年,现在又有种拿起刨子的感觉。”

人物简介
严红波
广东优筑工程董事长/工程总监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师

木匠最厉害
当年他差一点就去学了武术,严父写信请一位开武馆的高中同学收他为徒,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帯他走上匠人之路的是一位堂兄,“你这么聪明,不应该窝在家里。”严红波记得堂兄的这句话,他自承不算聪明,但是在堂兄给他指的这条明路上,他确有几分天赋。别人学做本匠至少三年才能出徒,他一年上手,已经能做出漂亮的家具,乡里首屈一指。“我很感谢我哥,那时候做木匠,第一年基本不做正经事,都是跟着师娘一起做农活,锻炼一年,但是我哥第一年就让我实际操作。做家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做2米的大衣柜和60公分的床头柜,在工艺上没有区别。相反做棺木有难度,做农具是难度最高的,能够做出来犁,就很牛了。”
说起木匠活来,严红波滔滔不绝,虽然见惯了造价干万上亿的大楼从无到有拔地而起,他还是觉得做木匠更厉害,“连船我都能造!”他享受这种手工活的快乐,创造的快乐,和后来城市中工匠的失落对比,这份职业有一种尊荣。“我们那里有古训,大家一起坐船,船翻了先救谁?老幼妇女病残之后,第一个就是手艺人,手艺人值钱。”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工程公司会去开办木器厂,在那里他感觉自在。
“他们的手艺我们都学到了,唯有一样,我们已经做不出那种木头结构的老房子。”他能享受建造的乐趣,欣赏建筑的韵味,并不在学手艺之后。孩童时代,他曾带着伙伴在长满青苔的祖屋穿梭追逐,在各种各样的游戏中踩遍了那些大人都已经遗忘的角落,画着画的碗柜,雕着花的床,都堆在灰尘和蜘蛛网里。白天,处处都有惊喜,到了晚上,聚在厅堂的天井,夏夜的月光洒在竹床上,有人把萤火虫放了出来,抬头看,银河清晰可见。
不是挎着国家地理帆布包拿着摄像机好整以暇,不是微信朋友圈上突发的情怀,东方人家就是严红波的生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祖屋是完备的徽派建筑,记忆里刚落成时十分精致,十七间房左右完全对称,除正堂屋外,其它各房间均向内外开门,空气可对流,然后各相邻房间也均有一道房门相通;所有屋子均为两层,二楼的阳台均为木筑,称为踩楼,也都相连。整个院落青瓦成遍,屋檐错落,天井阳坑俱全;墙砖少量为青砖打底,上方方 加筑泥砖;院内临天井的外墙多用谷糠拌泥糊面,再粉刷上青白石粉......
遥远的家
作为一个手艺人,严红波早就明白祖屋在他的记忆里到底是怎样一种象征,只不过在装饰施工这个行当打拼这么多年,他是第一次愿意拿出来讲给别人听:“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该更舒适,更符合我们的想象,可以传统,也可以颠覆传统,但最终应该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不可能去复制一栋徽派老屋,但是那种结构形式感,高大开阔的空间,对生活的关照,我们可以在现代建筑里重新实现,我希望家庭装修是可以传承的,它应该可以成为一种独特情 感记忆的发生场景。”
严红波的家在干里之外,他对家的想象,还要更遥远。
生在70年代的湖北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可以想象,除了读书他还得帮家里干活,那一代人的少年时光都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小伙伴们放学直奔田地,破破烂烂的书包往田埂上一丢,拎起锄头跟在父母屁股后头卖力气。葛穷不能阻止少年入兴致高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日益难懂的功课,甚至是老师的鄙夷,以及在学校的边缘化,都可以成为他们快乐的养分。但贫穷的阴影总是笼罩在生活之上,三百多天没心没肺的傻乐之外,总有几天,他们像大人一样忧心忡忡。一般是在8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城里打工的父亲结算工钱,会带回兄第俩的学费。当然,希望落空的次数居多,几次失望之后严红波和弟弟也有了经验,那天父亲回得早就万事大吉,要是大半夜还没回家,那一定是在包工头家里磨破了嘴皮,不肯放弃地等待最后希望,但结局早已注定。
父亲会强自镇定,瞩咐小兄弟俩跟老师多说几句好话,宽限几日,而小兄弟俩也只能硬着头皮,9月1号是他们的受难日,那种难为情的感受成为他日后奋斗的动力。在珠海当上包工头之后,严红波经同时跑过10个工地,重要工地每天去两次,其他工地两天次,每天7点出门,12点回家。当时他租了一套房子和妹妹同住,家里经常接到妺妹的电话:“我又有半个月没看到我哥了。”
他还记得离家时父亲的叮嘱:“过年争取带一干块钱回来,要是成了,今年杀一头猪过年。”1993年,那一年他19岁。这个任务不难完成,5月份他就機下了一干五百块。和《手机》片头的场景一样,村里用大喇叭通知邮局汇款,整个村子都知道他寄钱回家。在珠海忙碌的20年,工资一干五到一年一亿工程,严红波没试过停下来,催促他的从贫穷的恐惧,到父亲的期待,到乡党的赞赏,变成对伙伴的责任,对行业的使命。像每一个必须闯荡的少年,像每一个把思念藏在最深处的昇乡人,很久以后,严红波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他亲见多少高楼平地起,怀疑渐渐在现实里滋生,记忆激发着他的想象,他在坚持,但是又酝酿着改变。
中国人家
2009年他与珠海最著名的空间设计公司空间印象合作了优筑工程公司。旗下的木器厂、石材厂运转起来,在世邦还有一家瓷砖店。“尽量的,我们希望空间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进行一些功能空间的改造,有文化归属感,有感情,能生长,吸引家庭成员参与、沟通的空间,才能算是中国人家。我们做手艺的不喜欢讲大话,现在谈这些,因为我们不仅有理念有设计,能做工程,能落地。整个渠道已经打通,一般的定制需求都能满足。”中国人家,对于严红波来说并非空洞概念,它就是关于家的记忆,鼻腔和味蕾的几种记忆。长成之时,故园早被雨打风吹去,在踩楼下堆积的湿漉漉柴火,墙上斑驳的农业学大寨标语之外,他也看到了残存的窗、柱础、还有中轴线上的条石,但在他心中种下种子,让他日后有复兴旧观愿望的,绝不是这番质败景象,而是那鸡犬相闻,部里守望的温情。
屋外的大雪,火塘里黄色火苗烧到松节突然进发,手中的拨火铁钳、铁罐里飘出的饭香,时间停止了,少年渴望长大去外面美好世界间荡的雄心获得了片刻的平静一一那是之后从来没闻到的香味,从布满烟尘黑黝黝的铁罐里,就好像那间布满烟尘乌漆墨黑的厨房,代表着贫穷,却又安心,那就是家的味道。他念念不忘,“我马上有一家餐厅要开张,主打的就是这种味道。”餐厅的名字叫“小时候”。
在一个夏天傍晚,炎热没有消散,父亲回家了,他背着的,是一袋苹果。那是水果摊剩下的歪瓜裂枣,一块钱包圆。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用菜刀削去溃烂,一边削着,孩子们一边吃着。
“那一天,吃的真饱。”严红波露出了习惯的微笑。
 严红波和他的团队合影
严红波和他的团队合影